西域丝路上的中国器乐精神|道中华

通过有形表达无形,通过具体上升抽象。从古至今往来于西域丝路上的乐器不仅奏响了古韵悠长的千古佳音,更彰显出了中华民族亲仁善邻、温润仁美的精神世界。
丝绸之路是文明的和平共鉴之路,是东西方交流交往的大动脉。丝路精神根植于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和合共生、天地人和的中华文化“和”的基因当中,其气质在丝路大通道的核心区——新疆得到充分印证。
音乐是接天引地的人类精神艺术,乐器则是无形声响的有形之具。从鼍(tuó)鼓到纳格拉、从胡琴到艾捷克、从笙到手风琴、从唢呐到苏乃依,这几类有代表性的西域丝路上的乐器,在器物形制、文化脉络和艺术形态上均展现了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器乐精神。
作为礼乐器的“中国第一鼓”——鼍鼓,出土于龙山文化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自1978 年发掘至今,已发现鼍鼓八件。它预示着距今4300年前已形成华夏礼制的天地秩序雏形,中国千年鼓乐的篇章由此开启。

梳理丝绸之路中原鼍鼓与新疆纳格拉鼓之间的制作内涵和文化寓意,可发现西域与中原的血脉联络。鼍鼓的鼓腔以整段原木挖制,鼓面蒙鳄鱼皮。这种用天地之木配神兽之皮的制作手法,以明暗线的方式保留在新疆和中原鼓类后裔之中。
来自西域被称为铁鼓的新疆纳格拉鼓,保持了与华夏鼍鼓一致的整体制作工艺印记,它与鼍鼓的结构一致,材质却随着冶金术的影响变为铁质。与纳格拉鼓同属的还有藏族的达玛、傣族德昂族的抬鼓及花盆鼓、沙鼓等。这隐喻了华夏礼制文明的暗线。

与之不同的是,在千年礼制的影响下,中原鼓类在制作结构上发生了变化,但在材料上却保留了传统的木制,这凸显了华夏礼制文明的明线。鼍鼓作为万鼓之源、礼乐之基,续以中原鼓及纳格达鼓形而下之器载形而上之道的内涵。
因此,这个明暗线揭开的是中华文明“近者悦,远者来”的向心模式,是四方万民聚集中原相互交流的生生日新之意,更是何以中国的生命力所在。
古人将鼍鼓作为战鼓,纳格拉亦同样被系在马鞍上当作战鼓。因此,既有朱厚熜的“风吹鼍鼓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的气魄,也有王昌龄的“城头铁鼓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干”的风霜。纳格拉鼓与古代西域的羯鼓有着深层渊源,内在也呼应着古老的千年中华文明。

哈密艾捷克是哈密木卡姆伴奏乐器中的主奏乐器,广泛流传于哈密民间乡村部落。其形制与新疆其他地区的艾捷克有较大差异,类似中原的二胡,又被称为哈密胡琴。哈密地理位置独特,是丝绸之路上西域通往中原的“东大门”,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不言而喻,因此哈密艾捷克即可能是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过程中的产物。
中原的二胡与新疆哈密艾捷克形制特征神似,大体构造相同,存在较多的共同点。不同的是,哈密艾捷克多了一组共鸣弦。因此,有观点认为,哈密艾捷克就是中原二胡加上了共鸣弦,或是古老的艾捷克换上了二胡的琴筒。更有观点提及,哈密艾捷克就是西域传入中原的胡琴前身。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应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来自西域的胡琴汉化之后,在中国音乐传统中占据着核心位置。而哈密艾捷克是哈密唯一的高音拉弦乐器,二者都可以独奏和伴奏,也分别是汉族和维吾尔族乐器的代表性主奏乐器。
艾捷克最早起源于波斯,14世纪左右传入中亚,后进入喀什增加了共鸣弦。在整个南亚地区,都能看到辅助共鸣弦乐器的普遍使用。这里面有审美的需求,同时也许有制作工艺的要求。二胡不存在类似的问题,同样跟汉文化的生活环境及音乐审美有关。
在百年的历史长河中,这两种乐器蕴含的是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回流互授,哈密艾捷克的溯源有西域以西的脉络,但更能看到中原文化的深刻烙印。

笙是目前仍然在传承着的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也是中国唯一一件可以同时发出多个音的乐器,在音乐界被称之为“和声性乐器”。
笙在殷商甲骨文中,称为“和”。相传为女娲作笙簧,其音似凤凰鸣响,故有李太白“仙人十五爱吹笙,学得昆丘彩凤鸣”诗句。笙在殷商时期就在礼乐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隋九部乐和唐十部乐中的清乐、西凉乐、高丽乐、龟兹乐中均被采用,唐代是笙的鼎盛时期,涌现出许多技艺高超的名家。多声的特性、仙道的寓意,使笙成为国人之爱,民间宫廷均盛行。

在中外文明相遇的一千多年中,这件纯粹中原本土的乐器因其魅力催发出美妙的枝叶繁花。元忽必烈中统年间,西域回回国进贡的“兴隆(龙)笙”,实为鼓风式管风琴,将其称为笙,是因为形状结构与之极相似。十八世纪东西文明大碰撞,中国笙进入西方世界,由此促成管风琴音色改良、手风琴制造以及口琴的发明。
1777年,在华传教的法国传教士若瑟·马利·阿米奥神父把笙寄回了巴黎,让西方世界首次认识到了自由簧,并开始了一系列关于簧片振动的实验,不仅对管风琴音色的改良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更是催生了欧洲的自由簧乐器。
在笙“活簧发音”原理的直接影响下,1821年,德国音乐家布希曼发明了口琴。1829 年,奥地利的基里尔·达米安在原自动风琴的基础上设计制造出了第一把真正的手风琴,不久手风琴乐器风靡欧洲。
此外,20世纪巴扬作为手风琴家族一员,经丝绸之路返回“故乡”,在中国新疆形成独特的“俄罗斯族巴扬艺术”。新疆塔城市手风琴博物馆见证了这段历史,作为远古始祖笙的叶脉便如此在文明河流中蔓延生花,惠及东西方艺术文明。

“可道人间今古事,能学百鸟木中鸣。”中国人的一世,生也唢呐,去也唢呐。这个原本来自军中之乐的西域乐器,以穿云裂石之势刺破中原音声,成为生死共荣的华夏魂音。
唢呐在中国历史上存在多次传入的现象,早期用于军中之乐,后逐渐在民间普及。受文化选择和审美倾向的影响,中原唢呐与新疆唢呐存在较大差异。
新疆与中亚以及西亚的大部分属于干旱、半干旱气候,自然生态相近,因此新疆唢呐受到自然生态变化的影响程度很小,基本保持中亚唢呐原本的形制——较粗的杆子、无金属喇叭口,称为苏乃依。
随着清代对新疆管控的加强,清廷派驻官员与军队主要驻扎在北疆(伊犁将军),中原唢呐自然传入新疆地区(主要是北疆)。随着中原文化在新疆地区影响的加深,有的地方学习中原唢呐,出现了金属质地喇叭口的苏乃依。近几十年以来,甚至有些维吾尔族乐师用中原唢呐代替苏乃依,已经开始影响苏乃依特有的音律体系,并不断地吸取内地乐人的演奏技法。
19世纪,伴随新大陆华人华工的记忆,唢呐被带到古巴,成为圣地亚哥狂欢节上的游行声音灵魂。21世纪,华家乐班、周家班等成为当代中国民间吹打乐班的国际性旗帜,享誉海内外,他们代表的正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民间音乐之一。
“懒与笛琴争第次,一声开嗓地天惊”是唢呐的习性。吹出天地来世,跨越海域疆界亦是唢呐的命数。唢呐的来去既是天下疆域之格局,也是人间情怀之内里。

 孙晨荟,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从事宗教音乐、民族音乐、戏曲声乐研究。出版《雪域圣咏》《天音北韵》《谷中百合》《众灵的雅歌》等四部九十余万字的获奖学术专著;发表《新中国戏曲声乐学科理论与实践管窥——以孙清足的黄梅戏教学为例》(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戏曲剧种艺术体系现状与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等论文三十余篇。
孙晨荟,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从事宗教音乐、民族音乐、戏曲声乐研究。出版《雪域圣咏》《天音北韵》《谷中百合》《众灵的雅歌》等四部九十余万字的获奖学术专著;发表《新中国戏曲声乐学科理论与实践管窥——以孙清足的黄梅戏教学为例》(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戏曲剧种艺术体系现状与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等论文三十余篇。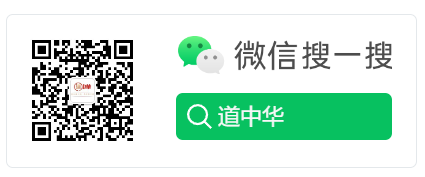
潘璇 编辑











 中央统战部
中央统战部
 中国政府网
中国政府网
 京公网安备11010102005982号
京公网安备1101010200598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