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罗:《蒙娜丽莎》和《兰亭序》有相通的美……|海外汉学家系列之⑥

——毕罗

记者:作为一名就职于中国高校的外国学者,您认为东西方在文明互鉴、交往交流方面还能够做出哪些有益的尝试?
毕罗:作为研究中国书法文化的西方学者,我一方面不断了解各种书法现象的文化审美价值,另一方面也在努力做出欧美人能够懂得的解释。
2021年,我在Routledge出版社出版了研究《集王圣教序》的英文著作。2023年2月,我即将在意大利出版全面研究《兰亭诗集》的意大利文专著,通过我的著作,积极地介绍广义的书法文化给国际读者,会有更多人意识到“书法文化是整个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一”这一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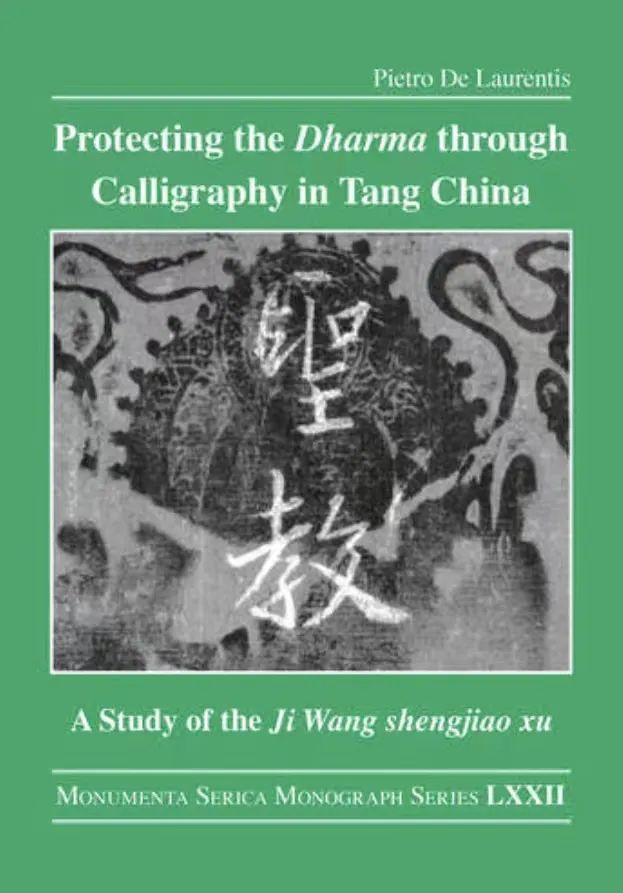
但是,认识到书法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能够真正欣赏它纯粹的“形体美”。西方绘画相当的写实,汉字书法不是具体写实形象的艺术,所以要真正欣赏它还需要对它的表现符号——汉字有深刻的认识。
但这并不是说,只有认识了几千个汉字以后才会对书法产生兴趣,才能够创作精美的书法作品。我本人的体会是,对汉字书法的感知在本质上就是“一见钟情”,这种对中国书法魅力的“着魔”一定不会是只有我这个欧美人才有过。关键在于,有了这么一种初步的“积极冲击”以后,如何更准确更有效地进一步认识它、欣赏它、消化它,最终把它当作自己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我非常喜欢中国古代书法理论中的一句话:“意在笔先”。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每次行动成功与否,都取决于起初的“意”,而实现这个最初之“意”,则需要漫长的时间和不懈的努力才行。研习中国书法,传播中国文化,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因此,我个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包括我所就职的广州美术学院在中外书写文化与美术交流研究中心所从事的活动,最终目标是促使国际文化交流,让中国书法以及其他有文化和审美价值的中国艺术走向世界,以便给全球人民提供内容更多元、形式更丰富的文化营养。

记者:2018年起,您在《书法》杂志连载了14期《书法行走——一个西方人游览中国书法文化》。这20多年的行走,对于您的意义是什么?
毕罗: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98年,真正意义的书法行走应该从那时算起。
我很欣赏中国俗语“百闻不如一见”。我认为,对于做学问的人来说,如果一直躲在自己书房里,久而久之就会养成忽视观察当下现实状况的习惯,以为所谓的“学术研究”可以充分解释一切现象。
第一次来中国,我十分渴望能够找到教我毛笔字的老师。我并不在乎什么名人专家,我想找一位民间书法爱好者。这种重视手头功夫和直接交流的心态深刻影响了我之后的整个治学态度。
后来,开始认真学习书法史的时候,我感到既然书法相关的好多文物都尚在,就应该尽量多看看实物。我那时候并没有所谓的“实地考察”的概念,只是比较单纯地想看看书法文化的真面目。
实际上,游览书法胜地时,由于交通和居住的需要还积累了种种体验,我也有意识地逐渐开始注意了一些与书法文化本身并没有直接关系的现象,比如说地理环境、当地人的生活习惯与饮食风俗等。我想,从纯粹的认识论角度来讲,“走万里路”和“读万卷书”都不能缺。
因此,这二十五年游览诸多书法胜地的经历给我带来了非常丰富的知识、经验和教训,不仅熟悉了书法文化本身,更重要的是了解到整个中国文化的面貌。对我来说,除了基本的学术规范,我做研究的最根本的动因和价值都来自于现实生活包括考察实地过程当中获取的种种营养和启发。

记者:您曾说:“要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就离不开书法”,如何理解?
毕罗:在今天的中国,书法活动主要是临摹和创作。民间爱好者和专业书法家都是结合这两种方式去从事书法活动的,只有一少部分对书法的历史感兴趣的人才会关注古代各种书法现象,成功地把书法实践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
读博期间有一段时间到浙江大学进修,我很快注意到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献和历史资料,并且意识到研究中国文明史的复杂性,也逐渐感受到这些文献的魅力。
研究敦煌遗书和佛教与书法的关系的时候,我注意到出于教育目的汉字石经或是歌功颂德的碑刻,实际上都是书法文化非常重要的部分。
可以说,中国人很早就开始注重书写汉字的形体美,古代社会需要公布某种“文本”的时候,不得不考虑把汉字写得尽量精美。虽然今天我们会觉得所谓的“书丹人”,也就是具体负责手写碑刻内容的人,只是一个制作层面的工匠。实际上,很多立在地面的石碑和埋在地下的墓志,其“书丹人”和出钱制作的人都考虑过关于书写美观的问题。
可以说,在研究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团体利用书法来弘扬佛法的史料时,也让我理解到“书法以外的书法现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这种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证明:第一,古代中国社会到处都是书法作品,普通人看招牌也好,墓碑也好,都能看到“公共书法作品”;第二,既然有那么多面向社会的书法作品,足以证明书法审美在古代社会当中的普遍地位。
西方有不少研究中国历史、文学、美术和宗教的学者,但是他们很少会关注到书法在中国古代社会当中的“普遍性”。我们现在看到的灯箱等电脑字体广告,其实在几十年前都是用手写的。
所以,要真正了解中国古代文化,根本不可能忽略书法与手写活动在古代所占有的文化地位。除了文人珍赏名作以外,有大量没写进历史资料中但一样伟大的“书法文化”,也需要我们今天的人利用当下的研究优势和条件去挖掘和重新发现。

记者:您曾经撰文《王羲之与达芬奇:两个中西美术传统的象征》,王羲之与达芬奇体现了东西方艺术家在审美与价值观方面怎样的不同?
毕罗:王羲之与达芬奇之间最突出的不同,是他们留下的艺术作品的语言表现和载体媒介完全不一样,最根本的差异还在于王羲之是用“毛笔”来创造出有不同文化含义的视觉符号的。
此外,在西方,不管是文艺复兴的绘画还是当代画作,规模都比书法作品大得多,这是与中国古代书法完全不一样的空间表现。另外,文艺复兴的画作还讲究静态的写实美,与组合笔画线条的汉字图像完全不一样。
我试图在文章中探讨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只要有一定文化修养的欧美人,如果要讨论画作,绝大部分人都会想到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东亚人要提出一幅艺术品,绝大部分人都会想到王羲之的《兰亭序》。既然欧美和东亚都会这么看重这两幅作品,它们所蕴含的文化含义必定很深。
真正的艺术并没有国界的,无论是哪种文化背景或民族信仰,无论探索“美”时的出发点和视角有多么不同,但只要有眼光的人都能欣赏到艺术品的美。
另外,我认为大众应当关注的并不是达芬奇的绘画成就,而是他为了研究某个实物或自然现象随时用铅笔画出的素描图像。严格地讲,他的意图并不在绘画本身,而是在为某种物理或生理现象造出一种“照片”。
在达芬奇的素描中有各种工程题材、人体和动物局部的作品,可以充分表现出一种“即兴”的绘画创作精神。这正好与历代欣赏的王羲之信札,即所谓的“帖”的创作精神一样。王羲之的书信并不是打稿或构思后的作品,而是因为人际沟通的需要随时兴发的书面交际的视觉成果,同样也是王羲之日常的生活和心态的写照。
我相信,东西方还有更多的美术现象可以进一步比较,除了认可它们的独特性和特殊性以外,更有趣的是发现它们之间的可比性和相通性。
(本文图片均由毕罗提供。)

卢旭 编辑











 中央统战部
中央统战部
 中国政府网
中国政府网
 京公网安备11010102005982号
京公网安备11010102005982号